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涉及鄂州古楼(古代称南楼,后称庾亮楼)的文章中,往往会提到当年庾亮镇武昌与部属登南楼咏谈的故事。故事说,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病逝于武昌后,庾亮接替了陶侃的职务,为征西将军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这年的秋天,天清气爽,景色清丽,佐吏殷浩、王胡之等人登上南楼咏谈,正当兴浓,音调渐入高亢时,听到函道中传来重重的木屐声,他们猜想,定是庾公。果然,一会儿庾亮便“率左右十许人步来”,殷浩等人想起身回避,庾亮忙说:“请诸位暂且留步,老夫于此事兴致也不浅。”于是便与殷浩等人共坐胡床吟咏,无拘无束地尽情欢乐。此事被刘义庆在其《世说新语》中记录下来,成为千古的“佳话”。殷、王二位是先于庾亮上楼的,那么,跟随庾亮上楼的“十许人”是些什么人呢?

目前在鄂州文史研究人员编辑出版的一些著录中尚没有发现一篇谈及此事的文章,为了研究鄂州文物、历史,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追溯。虽然刘义庆未在记载中直接点明上楼来的一些人是谁,但起码有一位重要人物在此之列,他,便是后来被人们尊为“书圣”的王羲之。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属山东省),出身贵族,两位伯父均身居高位。其一为王敦,是大将军,在庾亮之前曾镇武昌,其二为王导,是东晋司马王朝的丞相,当时有一句“王与马,共天下”的顺口溜,说的便是王敦、王导等王氏兄弟把持朝政的情况。王羲之早年从卫夫人(钟繇之徒)学书,后博览前代名家书法,采择众长,备精诸体。其草书“浓纤折衷”,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一改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便的新书体。他是中国把应用文字提升到艺术欣赏的第一人,于我国书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之功,其书作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书家中无与匹敌者,故有“书圣”之称。他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此后,贴学书家基本上是在王字的基础上按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等平和秀逸和王献之、李邕、米芾、王铎等敧侧跌宕的两条主线发展下来的。
王羲之咸和年间,正置风华正茂的年纪,其政治地位尚不高,在书法地位上也仅与庾亮之弟庾翼齐名(翼,在庾亮卒后替兄镇武昌),只是后来的名气超过了庾翼。《晋书》中记载:“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翼见而叹伏,与右军(即王羲之)书曰:‘吾昔有伯英(即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与庾氏兄弟、殷浩、王胡之等人关系密切,与王胡之还是叔伯兄弟,他们都是东晋的名士,个个能言善辩、吞吐不凡,在当时相互倾慕,彻夜长谈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年长且身份地位较高一些的庾亮更是以其超凡脱俗的风度而受到世人的尊重,所以,庾亮秋夜登楼咏谈赏月的“佳话”才得以流传下来。而王羲之书法被庾翼称为“焕若神明”,也绝不是一种夸大之辞。
鄂州的一些文史著录在记录这段事故时,往往只注重了前面的“佳话”部分,后面的记载却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若干年来的一件憾事。在《世说新语》中,刘义庆是这样说的:“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意思是说,后来,王羲之从武昌顺江而下到京城(即建康,今南京),与其伯父王导谈到这次庾亮与部属咏谈之事时,王导说,元规(庾亮字)的风度不得不稍受减损。在王导看来,身居要职的庾亮与下属不拘礼节的咏谈赏玩是有失风度的,而王羲之则替庾亮辩护道:“但是,他那种隐逸丘壑、超凡脱俗的高雅情趣还是存的。”王羲之本来也是一位很清高、很自负的人,能在作丞相的伯父面前对庾亮这样评说,足见庾亮的人格魅力非同寻常。
东晋成帝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社会较为动荡的年代,一方面王室南渡不到十年,北方十六国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南方的司马王朝也很不安宁,而王导在控制和维护司马氏政权中起到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王敦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排挤走了镇守武昌的陶侃后取而代之,随后发兵攻建康,逼死元帝,此事便得到王导的纵容。此时的王羲之,尚未成年。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历阳内史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兴反叛,由于陶侃等人的征讨,叛乱失败,王敦于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病死武昌,祖约叛乱也失败。王敦死后,陶侃从广州回来,复镇武昌这处战略要地,(陶侃送“菩萨金像”于武昌寒溪寺就是这个时候)。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也病逝于武昌凡口溪,庾亮便从京城赶来武昌接替了陶侃的职务,以征西将军领江、荆、豫州刺史的身份镇武昌。二十多年来,社会动荡不安,这个动荡时期也是王羲之走入社会的重要时期,当时社会,有一批象王羲之这样的年轻人,十分仰慕庾亮的为人,纷纷跟随庾亮,一方面是为了长长见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以便为将来的从政为官打下基础。武昌当时便有一批这样的人,或作庾亮的门客,或作小吏,或作幕僚,王羲之也便是其中的一位。当时,王羲之刚来武昌,任庾亮的参军(为僚属),后才升为长史,只是当时的地位并不很高而已,所以,在跟随庾亮上楼时,只被刘义庆以“十许人”而一笔带过。相反,在后来看起来名气并不很大的殷浩、王胡之反而记录在案而“名垂千古”。
古代是没有“专职书法家”的,王羲之也是这样,书法恐怕只是展示自己才能的一种方式,而做官才是官宦人家对子弟们的最终要求。回京城建康几年以后,有了在武昌跟随庾亮的这段经历,王羲之的为官之路也节节攀升,先任江州刺史,后又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称“王右军”。在会稽任上,终因孤傲的性格而与同僚不和,一怒之下,他称病辞官,隐居会稽,而著名的《兰亭序》就是在其辞官后的癸丑暮春(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写下的千古名篇。如果说王羲之继续为官的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仅多了一位平庸的将军;而他的辞官则是中国历史上又多出了一位杰出的书家,这既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千百年来不断引人思索的一个问题。

熊寿昌,男,汉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人。湖北省考古与博物馆协会会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员、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鄂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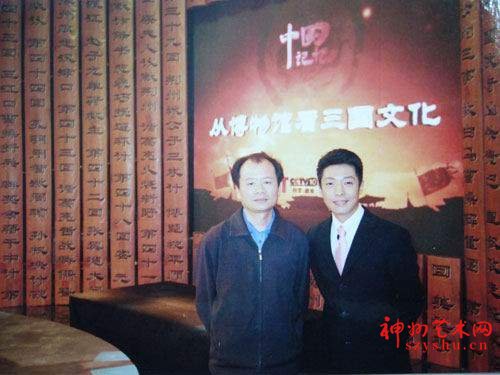
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南京艺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生班。鄂州市博物馆原党支部书记,副研究馆员,退二线后,专事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